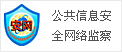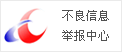2016年9月,繁星戏剧村,话剧《桃之夭夭》二轮演出6天,几乎场场爆满。
由莎翁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与首影(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这部话剧,推上台前的是清一色青春面孔,前来观剧的也有八成是年轻观众。
但这里上演的不是对青春成长无病呻吟的《小时代》,不是无厘头插科打诨的段子集锦,更不是搭配民谣诉说动物感伤的荷尔蒙派对。
而是一场情怀古早、趣味古典的荒诞讽刺剧。

【世界那么大,越狱去看看】
70后的编剧赵秀才,已经是整个团队的“老人”。作为戏剧主题情怀的奠基人,他把成长中见证的种种社会认识与发展曲折,投射在新旧交接的北洋时代,构筑起一个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戏剧舞台——“盲城”。
“盲城”并不是大世界的全部,剧中还设定了一个代表重视权利、法制健全的外部乌托邦——南方,但是却没有一个剧中人可以走出盲城。

为什么这些人只能活在盲城,沦为“盲人”?
三位主角构成的越狱共同体,是一套“盲点”类型学:一根筋农民李柱子,人生理想就是抱着媳妇“吃口桃”,只会习惯性的盲从;骗子商人朱时髦,怀着别人有的我也要的不甘,行事“不讲究”,从而成为坏秩序的一部分,因为怕光他只能留在原地装盲;留洋书生郑经,走得又太急太快,人权还没实现就高唱“狗权主义”,他的盲目在于他对复杂人性、漫长过程还远远没有看懂。
越狱共同体的每个人,说起自己理想时都是感情饱满、正义凛然,对自己理想有利时便同舟共济,当自己理想受挫便会毫不犹豫去攻击、排挤、揭发他人。是不是就像“小时代”里的我们?

但这一次,“盲人”们的个人情感在荒诞的演绎中被间离,观众在欢笑的同时,开启了自省。“世界那么大,越狱去看看”的口号原来不是像海报中看着那么文艺,越狱不是“生活在别处”式的旅游广告,而是一次启蒙的呐喊:Just run away!
观众醒悟,这部戏讲的是格局。
【小舞台的大格局】
剧本建立了一个充满隐喻的文本模型,要转化为一个质感扎实、色彩丰富、层次饱满的沉浸式演出,需要团队中每个人都完全地调动脑力提供创意。有趣的是,各个主创人员的创作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导演葛鹏翔,在舞台上着力营造着一个想逃,却无处可逃的悲剧世界。她脑中有一个巨大的框架,像一个枷锁一样牢牢的锁住所有的事物,坚硬如铁,纹丝不动,所以舞台上立起了一个大的钢架,悬挂黑布,给人视觉上的冲击和延伸。检票口也放置了一扇监狱的铁门,让观众在话剧开演前就感受到前奏气氛。最重要的监狱场景,她用钢架和铁皮拼成了一个牢房的场景,景片线条扭曲又张扬,顶部有扇不可触及的小窗,窗中投射着微弱光芒,却支撑囚犯马不停蹄挖通地道。

导演葛鹏翔本身就是演员,首影集团签约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研究生,在电影《麦客乔丹》拍摄工作结束后,很快就开启了话剧《桃之夭夭》的筹备以及排练。导演葛鹏翔为这个悲剧披上一件欢乐的外衣。《桃之夭夭》中穿插着大量后现代式的舞台探索,民族歌舞、迪斯科、电子游戏模拟等片段的插入,不仅强化了舞台叙事中对人物情感的表现力,也为主题渲染着一个百感交集的现实通感。当然,作为一个要对市场效益负责的新导演,葛鹏翔更想让习惯了高密度、快节奏信息接受方式的年轻观众,能被频繁唤起新的兴趣点。
老艺术家谢樑作为艺术指导,则一直雕琢着剧中的表演,试图在这出符号堆叠、象征频出的年代荒诞剧中,添加上血肉感、烟火气。经他指导,即使是那个出场极短的马大帅,也极为惊艳。虽然至始至终马大帅威严端坐的画像都陈列于画面中心,人们言语间对他的权威极其敬畏,可出场时却是一个矮小、尖嗓、婆妈、秃顶的形象,巨大的形象落差产生了爆发的笑果和激烈的讽刺,与卓别林在《大独裁者》的黑色幽默有异曲同工之妙。
执行制作人叶阳坦言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导演,编剧以及监制演员们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汗水,当然,还有各位演员和其他创作者的集思广益,都融合在了这出小而复杂的戏剧里。开场时,入场观众的衣服被贴上“囚”字标识,狱卒直接走下舞台对观众训话,拉起了一个笼罩所有观众的牢笼,这是最流行的沉浸式演出手法;闭幕时,被屠杀的平民消失在幕后,两个罪恶的小人偏偏起舞,如同电影《索多玛120天》结尾那样,将罪恶凝滞在看似美好的生活表像中,又是最经典含蓄的文学语言。
一切融合都不露痕迹,不是《暗恋桃花源》那种二元对比,而是一种多元的有机混搭。要再描述得具体些,应该说是骨骼、血肉、皮肤、外衣等元素的层层叠加。所以,《桃之夭夭》比起传统话剧,更像一个叠加了儒家教育、民主教育、契约教育、成功教育……的现代人。
这是一个小舞台的作品,却不是小作品。从文本内容到创作合成,《桃之夭夭》对多元时代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我们需要突破小时代的我,翻越“我”身上的墙,从大广角看大格局。

【小剧场里的美好星球】
一直致力于“为中国之美好而做电影”的资深电影人葛宏伟在策划话剧《桃之夭夭》时,坦言他对剧场演出的投入基于两个方面的战略眼光:商业效益,社会效益。

在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15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里,经历了2014年的调整期,2015年中国演出市场逐渐回暖,更趋理性,涌现出一些新业态,行业更加重视创新和作品质量,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将目光投向演出领域。从各项统计和分析来看,话剧市场的票房收入上升幅度明显。
《桃之夭夭》在商业效益上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制作人陆培志说,不仅首演期间场场爆满,周末现场甚至还应观众需要,现场以非折扣价加售戏票。可以预期,该剧将在首演结束不久后,展开更大规模的巡演。

而这,只实现了葛宏伟商业效益战略的第一步。《桃之夭夭》作为首影(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影孵化项目的第一个作品,将在剧场演出中广泛吸收建议,最终打磨成一个内容可解读、趣味接地气的院线电影。
同样,《桃之夭夭》也是其社会效益战略的第一步。剧中关于多元社会格局观的思考,则是首影(上海)“美好星球”规划探索和构筑的起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发展,将是中国乃至世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主题。尽早以史为鉴,少走弯路,既是该剧对观众深层的提醒,也是一个未来文化地标的奠基。

《桃之夭夭》演出第二晚,北京迎来入汛以来最大暴雨,许多观众衣服、鞋子全都淋湿仍持票而来,奇迹般的达到过半上座率,全体演职者都深受感动。虽然剧场外大雨滂沱,剧场内却热情高涨!
《桃之夭夭》演出第四晚,现场来了一个庞大的少年观演团。主创者们没想到有这么小的观众,也担心他们无法理解剧中的内容和手法。但小观众们看完,紧紧围着不舍离去,他们眼里闪着清澈的光,把舞台上的演员当做大明星来崇拜合影。
因为有光,逃还是不逃,不是问题了。

《桃之夭夭》锦灰堆
赵秀才
《桃之夭夭》原来叫《越狱》,因为那什么的原因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为何会有“越狱”这种东西的初衷?起因是姜文先生的《让子弹飞》。
那年冬天——应该是冬天,因为大概记得看完《让子弹飞》回来路上,而今已经定居加拿大借了我钱还没还的朋友吸溜吸溜着鼻涕嘴里冒着哈气问我,你也是编剧,能不能写出这么牛逼的剧本?我吸溜吸溜着鼻涕说,没戏,这么牛逼的结构喜剧加深刻政治寓言,太难了,也就姜文干得出来,我怎么可能?
我口不应心。
后来跟我师兄史鹏瞎扯淡得知一个消息,居然《肖申克的救赎》超越了《教父》成为IMDB排行榜的第一名,我愤怒于小清新影迷们的审美文化和他们那种鸟鸟(音DIAO)的文化自我陶醉,便想恶搞一下《肖申克》,于是便有了《越狱》,我想讲一个黑色幽默的寓言,搂草打兔子指桑骂槐肖申克。
写作时候正痴迷于民国史,而现在的和谐社会又绝对没有越狱这种负能量事件发生的,所以便将剧本发生的时间放在了北洋,然后一切都顺利了,人物、事件、灵魂黑夜构建等等,都顺理成章,一秃噜到底。
剧本5年后,终于可以将《越狱》即《桃之夭夭》付诸话剧排练了,我很激动。
生在这片热土上的编剧普遍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剧本之后的创作团队根本不鸟剧本,我就生活在这片热土上,所以我担心鸟不鸟,后来惊喜发现,监制、导演、演员、制作人、制片,都鸟剧本,而且很鸟,我很激动。
永远都忘不了他们排练的日子,这种日子是我一生都可以值得嘚瑟的时光,因为我亲眼看见导演监制他们软硬兼施逼迫演员们一个字一个字把剧本上的文字变成了活生生的对白,一点儿都不许错,语气、节奏更不许出问题,甚至还增添了N多的改进想法,场面调度更是我从未想过的,虽然演员们住宿饮食条件很差,一段时间还囚在朝阳宾馆地下室比盲城监狱还劳改农场,可我很激动。
我亲眼看着王刚逐渐变成了郑经,张明敏逐渐变成了李柱子,管博文变成了朱时髦,裘恩典变成了绿茶婊陈佩诗,导演葛鹏翔变成了典狱长,匡玲萱变成了翠花,马路变成了金宝,郭振跃变成了马大帅,我自私自恋地告诉自己《桃之夭夭》已经从我的大脑右半球皮下灰质里跳出来,独立自主了。
一个桑拿天的晚上,我写完了当天的任务剧本,去看他们排练,后来骑着破自行车靠右行驶在昌平县城月黑风高回家路上,在遵守交通规则等待红灯变绿一只脚踩在马路柏油上一只脚踩着脚蹬子上偶尔才有一辆汽车飞驰而过根本不知道我何许人也的时候,回想着他们的第一次联排,突然就有了一种即将分娩的幸福,除了当时气温高湿度大汗液排泄不畅热量长期积聚体内散不去。
终于,繁星戏剧村2剧场了。
我特务一样潜伏在观众群的最靠边座位上,忐忐忑忑观察着他们的反应,龌龌龊龊看着他们被台上演员们逗得前仰后合,我盲目自信地宣布,《桃之夭夭》在这个星球上在这个刹那间,吸溜吸溜地存在了,而且冒着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