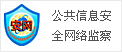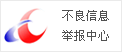一、“钱锺书斥责马悦然”
多年以来,在中国媒体(包括纸本报刊和网络)广泛流传着一则“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话。这则话虽然被广泛引用和传播,却因为引用者都不注明出处,最终成为疯传多年的“无主信息”。这种“无主传播”状态,使“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真实性丧失殆尽,如在新浪微博中,网友“云梦子围炉夜话”就在与马悦然现任夫人陈文芬交流时说道:“我百度了一下,虽有多家报刊转载此事,但皆未言及来源,实属可疑。我借用此轶事,无非是为中国文学鸣不平,无丝毫贬损污蔑钱先生之意。”(2011-10-2)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它表明受众难以采信“钱锺书斥责马悦然”这则信息——实际上,其无主传播越广泛,其可信度越微小。
然而,这则“虽有多家报刊转载此事,但皆未言及来源,实属可疑”的“钱锺书斥责马悦然”信息,真是无中生有的“网络八卦”吗?不是!在《传记文学》1995年第1期中,张建术撰写的报告文学《魔镜里的钱锺书》有这样一段话:
更早的时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上府拜访他,那次,钱锺书一面以礼相待,一面对着大名鼎鼎的马博士,说出一番尖锐的话来。他说:“你跑到这里来神气什么?你不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饭碗吗?你懂中国吗?【你会说几句中国话,不就会说‘你好’、‘你吃了吗’这么几句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那钱是你给的吗?】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被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评】,有这道理吗?”
[引者按:作者张建术告知,《传记文学》版《魔镜里的钱锺书》为作者朗读手写稿,时任《传记文学》副主编刘向宏电脑录入,与原稿文字有个别出入。应作者要求,本处引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魔镜里的钱锺书》中相关段落,其中,前两处“【】”中文字为《传记文学》中没有,后一处“【】”中文字与《传记文学》中相应文字语句顺序前后颠倒]
上面这段话,就是“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原始出处。《魔镜里的钱锺书》在《传记文学发表》后,张建术应邀对此文作了剪辑压缩,以《做聪敏的君子——侧记钱锺书》为题目在《大学生》杂志1996年第1期发表,这段话原文刊载其中;《中外书摘》1996 年5 月号和《科技文萃》1996年第7期先后以《聪敏君子钱锺书》为题目摘要转载这个压缩稿,这段“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话仍然刊载其中。
然而,我们现在网络搜索中,所能搜索到的这段“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文字,均无作者、无出处,变成了难以采信的“无主信息”。
二、马悦然夫人的否定
这则原出于张建术著《魔镜里的钱锺书》的“钱锺书斥责马悦然”文字,自发表以来,被广泛转载和传播,特别是2000年后网络普及以来,它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信息。近年来,伴随着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强化,更加以马悦然以“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身份在中国公众视野中曝光度的日益提升,“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信息传播也逾加普及。但是,因为它在媒体中被演化为“无主信息”,就导致了无论引用者、还是接受者都对之持“似是而非”的态度。
正是在这个语境下,马悦然现任夫人陈文芬(实名认证“小妖陈文芬”)于2011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期间,以回复网友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发出10则微博,明确否定“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可能性。陈文芬的主要观点表现在如下微博中:
回复@舍心忘兹:很多人利用传言,藉钱锺书之口来伤害马悦然。我认为:传言中伤的不是我丈夫,而是钱先生。以钱先生之学养风范,谦谦君子,他能说出如此鲁莽无礼,缺乏常识的言语,对待一个外国书生,钱锺书是钱锺书先生,他可不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啊!2011年9月29日
回复@舍心忘兹:马悦然1981、1982年两次拜访钱锺书,杨绛先生皆在场。那一系列拜访中国文人的活动,进行录音采访,有档案。我不忙于驳斥谣言;令马悦然难过的是,怎么会有人利用故去的钱锺书,来讲粗鄙无聊的闲话,他们那一代人受苦还不够吗?2011年9月29日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土耳其帕慕克获得诺奖,也有英文与其他语文译本的;这奖是瑞典学院十八名院士来评论,瑞典人学过欧洲几种主要语言,日文,中文对他们来说,就远得多了。评委需要译本是常情常识,钱锺书先生不至于连这样的事都不明白,谣言伤害钱锺书至此,文人集体悲哀。2011年10月2日
回复@云梦子围炉夜话:当年马悦然、陈宁祖夫妇赴北京钱府拜访,两次见面杨绛先生也在,并无外人座陪。谈话主题是马悦然手中的研究大计划,就学术跟作者的视野,马悦然希望知道加进“散文”这一文类于学术计划,钱先生的看法如何?全程未谈过诺贝尔文学奖,更无谈过巴金作品。2011年10月2日
回复@云梦子围炉夜话:马悦然欣赏许多中文作家作品,惟从未翻译过巴金作品,无论是英文或瑞典文;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毕其一生于文化语言翻译贡献卓著,不会不知道诺奖评委须要译文阅读亚洲语系文学作品,此等谣言中伤仙逝多年的钱先生,马悦然活着的人为故友难过。2011年10月2日
从时间比对,钱锺书与马悦然见面,不能谈及诺贝尔文学奖。彼时,马悦然如何能想到自己成为诺奖评审,天方夜谭啊。2011年10月3日
归纳上引微博,陈文芬否定“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可能性的主要论据有:(1)她不相信钱锺书“能说出如此鲁莽无礼,缺乏常识的言语,对待一个外国书生”;(2)马悦然和已故前夫人陈宁祖两次拜访钱锺书是“一系列拜访中国文人的活动,进行录音采访,有档案”可作证;(3)马悦然没有翻译巴金作品,钱锺书不会针对他指责巴金作品翻译问题;(4)拜访钱锺书时,马悦然尚不是诺奖评委,钱锺书不可能用未来的事指责马悦然。
陈文芬的“否定”,不无道理。但是,有如下可质疑处:
其一,她主观性地将这则“钱锺书斥责马悦然”认定为“如此鲁莽无礼,缺乏常识的言语”,其他读者未必认同,钱锺书本人也未必认同。
钱锺书对人对事的严谨不苟、直言辛辣,是世所周知的,他如果看出马悦然“就是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饭碗”,是绝不会隐而不发的。陈文芬女士如果花点时间阅读一下钱锺书自己的论著和其友人关于他的文字,就会了解钱锺书的“狂者胸恣”。
陈文芬认为“(诺奖)评委需要译本是常情常识”,她持这样的“诺奖常识”显然是把诺奖评委本身的语言缺陷变成了不可质疑的“天理”了。如果诺贝尔文学奖真正是“世界性”的文学奖,为什么非西方文学语言必须“转译”才有资格参评?文学的学识(不是诺奖的常识)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语言在根本上是不可能通过翻译而不被损害的!这个文学常识,陈文芬女士大概不懂得,但是钱锺书是必然懂得的。
其二、陈文芬没有搞清楚“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文中针对性。
在“钱锺书斥责马悦然”中,有如是说:“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那钱是你给的吗?】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陈文芬指出,马悦然1985年才入选瑞典学院院士和进入诺奖评委会,而他拜访钱锺书在此前,“从时间比对,钱锺书与马悦然见面,不能谈及诺贝尔文学奖。彼时,马悦然如何能想到自己成为诺奖评审,天方夜谭啊。”
然而,在“钱锺书斥责马悦然”话中,并没有认可马悦然是诺奖评委的含义,相反是对马悦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有质疑,所以才会质问道“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如果我们考虑到钱锺书知识的渊博和掌握信息的及时广泛,而且采信这句话是钱锺书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合情理的推论:钱锺书得知尚不是诺奖评委的马悦然在中国自称诺奖评委,所以对他发出了这样的批评和质问:“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那钱是你给的吗?】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因此,陈文芬仅以马悦然当时不是“诺奖评委”否定钱锺书上述批评的可能性,是站不住脚的。张建术《魔镜里的钱锺书》文中记述所指此事发生的时间,也是在1985年之前--马悦然进入诺奖评委之前,这是与“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的质疑是吻合的。
“巴金的书被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这句话是举中国文学翻译成西文而受损害的一个例子,其中没有文字指出是批评马悦然把巴金作品翻译烂了。因此,陈文芬用马悦然从未翻译巴金作品来否定钱锺书说这句话的可能性,理由也是不成立的。如果陈文芬联系到下面一句话“【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评】,有这道理吗?”,就应当明白,批评“巴金作品翻译烂”的主旨不在批评马悦然,而是针对“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评”的“诺奖规则”(即陈文芬所谓“诺奖常识”),目的是要指出这个规则“没有道理”。
其三,以拒绝录音采访为惯例的钱锺书,是否会破例接受马悦然的“录音采访”?
陈文芬声称马悦然拜访钱锺书,“进行录音采访”。这个“录音采访”,是不符合我们所了解的钱锺书对待采访的态度的。光明日报记者单三娅在1999年7月16日发表的《钱锺书、杨绛与光明日报》一文中记述说:
1988年5月,在新闻改革的大形势下,报社编辑部组织记者采访一些文化名人,就如何办好《光明日报》发表意见。文艺部研究后决定采访钱锺书、夏衍、唐弢、萧乾。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史美圣还有摄影记者彭璋庆来到钱先生家。那天他首先把我们让进他们的客厅兼书房。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又重申了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意思,同时客气地对拿起相机准备拍照的彭璋庆说:“我不喜欢记者照相,大家坐下来聊聊吧!”彭璋庆只好放下了相机,从始至终成为一个旁听者。……那天他们夫妇二人还对翻译界的现状谈了看法,批评了不严谨的风气。那天谈得很投机,最后钱先生同意将他对报纸改革的意见整理好给他过目后发表。几天后,史美圣将我整理的小文寄给钱先生,请他定稿,过了一、两天,钱先生将改稿寄回,并以他一贯幽默宽容的笔调附一毛笔短信:“美圣同志:来函奉悉,三娅同志记录得很中肯扼要,把我的废话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遵旨改几个字送还。”
单三娅记述的采访情景,与《文艺报》前副总编吴泰昌记述的另一次采访情景非常一致。吴泰昌1977年首次拜访钱锺书先生,至1985年时,已经是可以“不告而至”的钱府座上客。但是1985年冬天,他带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采访时,情景也是如此:“记者采访时我一直在场,钱先生不同意记者录音、作记录。后有机会看到‘速写’的原稿,又见到钱先生的修改稿,对照一下,经钱先生的‘回忆增补’,确实使文章添了‘实质’的内容。钱先生‘瓮中捉鳌’点睛之语,被记者采用为文章的正标题。”(吴泰昌著《我所认识的钱锺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林湄采访完成的报道《“瓮中捉鳖”记——速写钱锺书》当年发表在香港《明报》。该报道记述了这次采访时相同的情景。
钱锺书拒绝“记者录音、作记录”,旨在坚持对采访稿“过目”、“修正”的权力。他既然对单三娅、吴泰昌这样熟悉的记者、朋友的采访都拒绝录音、照相,何以为对外国人马悦然网开一面呢?因此,对于陈文芬所声称、而且她自己表示并未有查阅的“采访录音”,我们有理由质疑其“存在”。
其四、陈文芬不是当事人,却在没有做必要的调查研究和掌握基本凭据的前提下,擅自为当事人“作主张”。
据张建术的报告文学记述,“钱钟书斥责马悦然”发生在1985年之前。马悦然前夫人陈宁祖1996年去世;陈文芬于1998年与马悦然初识于台湾,“密恋”多年,2005年宣布婚讯。(《马悦然与陈宁祖、陈文芬》,羊城晚报,2012年11月18日)从时间比对来看,1980年代发生在钱钟书与马悦然交往中的事情,陈文芬完全不是知情人。
在2011月10月2日微博中,回复网友“云梦子围炉夜话”所言“我百度了一下,虽有多家报刊转载此事,但皆未言及来源,实属可疑”这则微博时,陈文芬说:“回复@云梦子围炉夜话:好感谢您这样说。”陈文芬这个回复表明,她与这位网友一样,并不知道“钱锺书斥责马悦然”有正式的原始文献出处——《传记文学》1995年第1期。她是在没有对信息来源作考查、并且掌握其真实来源的前提之下,针对一个“自以为无主”的网络信息作回应。
在2011年9月29日微博,陈文芬指出:“马悦然1981、1982年两次拜访钱锺书,杨绛先生皆在场。那一系列拜访中国文人的活动,进行录音采访,有档案。”但是,在2011年10月3日微博中,她又声称“虽我未及查阅详细的日期,我可以肯定两人谈话绝不可能涉及诺贝尔文学奖”。这两则微博告诉我们:陈文芬本人不仅没有查阅过她声称的马悦然采访钱锺书的录音档案,而且连所称“采访”的日期都不知道(“未及查阅详细的日期”)。既然如此,她关于采访内容的主张(“我可以肯定两人谈话绝不可能涉及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无根据的臆断妄言了。
退一步讲,即使陈文芬所声称的“录音档案”证明她关于这两次钱马会谈情况的言论属实——“不能谈及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仍然不能因此排除“钱钟书斥责马悦然”的可能性。因为,1998年才与马悦然“初识”的陈文芬,不能排除马悦然在1980年代有第3次或更多次拜访钱钟书的可能(王元化《一九九一年回忆录》的记述可见这种可能性,详见本文第四节),自然她也不能排除在她所指称的这两次拜访之外发生的事情——“钱钟书斥责马悦然”。
作为非当事人,陈文芬如果是负责地甄别历史信息的真伪,她应当提供相应的事实材料为自己的立论作证据。否则,她的“钱锺书与马悦然见面,不能谈及诺贝尔文学奖”就真的是“天方夜谭啊”。
三、钱锺书究竟怎样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前文述,1985年冬,作为钱锺书先生忘年之交的吴泰昌,应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之请,带着后者对钱锺书先生进行了一次不告而至的采访,钱锺书戏称为“瓮中捉鳖”。林湄在香港《明报》发表了关于这次采访的报道《“瓮中捉鳖” 记——速写钱锺书》。其中,与本文相关的是“钱锺书谈诺贝尔文学奖”。相关文字全录如下:
话题从文学创作谈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没想到这个看来并不新鲜的话题,却引出了钱老一段精彩的议论。他问我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萧氏说:“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说活着的,在已故得奖人中有Grazia Deladda,Paul Heyse,Rubolf Eucken,Pearl Buck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去年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二十年采访选》,翻到J-J Borges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的那一节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心,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太看重了。”(此段引号内的回答,是钱锺书在修改稿上亲自写的——笔者注)(因在内地无法查找当期《明报》,转引自《我所认识的钱锺书》第55页)
吴泰昌在《我认识的钱锺书》一书中介绍,在他征得钱锺书同意后,他将上引《明报》内容采用“新闻摘要”的方式于1986年4月5日出版的《文艺报》刊出,刊发标题为《著名学者钱锺书最近发表对“诺贝尔文学奖”看法》,全文如下:
“萧伯纳说过,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著名学者钱锺书是在寓所接受中新社香港分社记者采访时,发表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他说:“只要想一想,不说生存的,在已故得奖人中有黛丽达(Grazia Deladda),海泽(Paul Heyse),倭铿(Rubolf Eucken),赛珍珠(Pearl Buck)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在谈到博尔赫斯(J-J Borges)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一事时,钱锺书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心,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又太看重了。”(引文英文名字为引者附)
从林湄的报道和吴泰昌的记述,都可以见证,钱锺书对于自己发表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是非常严格谨慎的,公之于世的文字,凡以他本人名义,他都要求书面审阅、订正。尤其要注意的是,他事后与林湄、吴泰昌的通信表明,他不仅事前要审定相关文字稿,而且事后是关注社会反应的。(参见《我所认识的钱锺书》,第58-59页)
四、钱锺书对马悦然的真实态度
钱锺书究竟怎样看待马悦然?从笔者能够查寻到的文献来看,大概可以说,钱锺书与马悦然交往之初,对后者是比较接受的,但是在进一步的交往中,他改变了对马悦然的看法和态度。
王元化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指出:“我和马悦然相识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钱锺书介绍给我的。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锺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锺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学术界》双月刊),2001.2)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从王元化的记述可见,他与马悦然的关系始终是友好、融洽的。因此,他介绍钱锺书与马悦然关系“交恶”、钱锺书指出“他(马悦然)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是有可信性的。这可以作为张建术报告文学中关于“钱锺书斥责马悦然”记述的可信性的一个旁证。
另一个旁证,是国际著名的计算语言学先驱钱定平教授在《斯人难再得——缅怀钱锺书》一文中写道:“关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外文‘烂译’,锺书先生对瑞典的马悦然曾经有过一番少有的‘耳提面命’ 的谈话。这大家都知道。”(《出版广角》,1999.2)钱定平所谓“少有的‘耳提面命’”就是指“钱锺书斥责马悦然”。钱定平少年时代就是“钱迷”,并在钱锺书生前与其有书信往来,以他的国际视野和对钱锺书的认知,他能够采信此说,并且承认“这大家都知道”,是对“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真实性的一个有价值的旁证。
五、“钱锺书本人看过这篇东西”
在考辨“钱锺书斥责马悦然”,为本文作资料准备的时候,我通过文化艺术出版编辑寻找到了《魔镜里的钱锺书》的张建术的电话,并在电话中向他作了咨询。他告诉我,早在陈文芬之前,已经有人对这篇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称之为“小说家言”,针对这种质疑,他撰写了《〈魔镜里的钱锺书〉是小说家言吗》(未刊稿)。他通过电子邮件提供了这篇写于2010年12月8日的文稿,并表示允许我在将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自由摘引文中言论。现摘要如下:
最近看到网上有文章指责我的那篇《魔镜里的钱锺书》是小说家言,不足凭信,并以一处小错为据。初时我付之一笑,近日想想还是交代几句比较好,算是对读者负责。
我本人确实写过小说,现在还准备写,但不等于我写的报告文学就是小说家言。两种文体的区别我很清楚,做起来自然各行其道。实际情况是钱锺书本人在世时看过这篇东西,未着一字不认可,倒是指着挑他毛病的段落说:“这些地方都挺客观。”他本人都不说我是小说家言,别人凭什么这么武断?
当时这篇报告文学的出炉,有它一个特定的背景。第一是杂志社向我约稿,我答应人家了。第二是当时有人把整人诬陷的矛头指向了钱锺书和他的朋友,制造了局部的白色恐怖。钱锺书1994年、1995年两度生病,直至发烧住院,跟这场风波不无关系。这事在当时不是什么秘闻。
说我做小说家言的人,是不是清楚上述写作背景呢?谁会相信钱锺书本人愿意别人拿他的真名实姓做小说呢?那时候他活着,是有能力出来说话的,有谁见他否认过文章的真实性呢?
张建术在电话中告诉我,《魔镜里的钱锺书》文稿经电脑录入打印后,由杂志社方面提交钱锺书亲自审阅,钱锺书认可后告知了张本人,并发稿刊印,这就是“实际情况是钱锺书本人在世时看过这篇东西,未着一字不认可”所言。张建术还在电话中告知,“钱锺书斥责马悦然”,是他在准备《魔镜里的钱锺书》的采访过程中,三次从不同的人物口中所听到的,三次的内容是一致的。在电话交谈中,张建术还特别说明,他撰写这篇报告文学,是在钱锺书遭遇“特殊困难”时期受约于杂志社,并且当时承诺不向外公开杂志社约稿的背景——“当时有人把整人诬陷的矛头指向了钱锺书和他的朋友,制造了局部的白色恐怖”。
依据张建术的《〈魔镜里的钱锺书〉是小说家言吗》一文及他与我的电话交谈内容,我们能否采信“钱锺书斥责马悦然”的文字是“经钱锺书过目并认可”之说呢?作更进一步的直接取证超出了笔者的能力。但是,本文前述林湄、吴泰昌、单三娅所披露的钱锺书对采访、报道的态度和作法看,在钱锺书生前存在了近四年、传播极广的《魔镜里的钱锺书》要逃出他的“法眼”是不可能的。连侨居海外的文学界外人士钱定平承认“钱锺书斥责马悦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当事人钱锺书岂能闭目塞听?因此,我是倾向于钱锺书对张建术《魔镜里的钱锺书》的审定和认可的。否则,我们是应该闻见对自己发表的言论“字字计较”的钱锺书的相关否定反应的。
六、我们还需要“钱锺书”吗?
学者吴泰昌记述他1980年造访钱锺书,在参观了钱先生书房以后,与钱先生有这样的对话:
在与钱先生杨先生用餐时,我说别人都说你过目不忘,钱先生摆摆手,他说:怎么可能做到过目不忘呢?我只是没有藏书的习惯,看了书尽可能将有用的东西用脑子记下来,用手抄下来,万一需要时再去重查。我对自己的著作不断修改,除改正误排的,补充新发现的材料外,也有改正自己发现或别人指出的误引或不恰当引用的。我说,过目不忘你不认可,那说过目难忘总还可以吧。他还是摆摆手,不作回答。(《我所认识的钱锺书》,第87页)
钱锺书在生的时代,做学问主要还是靠读纸本书为主。他不喜藏书,“书非借不能读也”,就靠频繁借书阅读做学问,当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多称他“从所图书馆里借书多,还得快”,而夫人杨绛说:“钱先生有书就赶紧读,读了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多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在当今的计算机和网络做数据存储的强力工作时代,钱锺书式的苦读穷究似乎没有意义了。他当年写《管锥编》时“窝居”于社科院文学所办公室,用小推车借阅图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费尽心血劳力才能获得的信息,我们现在可以在万维网中便捷地检索到。但是,我们在方便之中养成的是马虎,在丰富之中得到的是恍惚,我们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有了无需尊重原作、原创,连出处和作者都忽略,只保留赤裸而无主的“信息”。“钱锺书斥责马悦然”就是这样一则被网络时代“无主化”的信息,这个信息的虚化和无意义化,表征的是当代学术的轻浮功利,而它的要害就是钱锺书所代表的学术精神的丧失。
丧失钱锺书精神,我们只能沦为信息浮乱中的睁眼文盲——我们知道一切,但一切都是虚实莫辩,真假倒置。世间恨失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