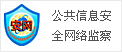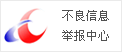导语:对于语言的探索是永恒的问题。语言是最初存在么?语言的界限在哪里?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什么?语言为什么会腐烂?……当然在日常言语之中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无意义”,甚至“现实无力感”出现的时候,这些关于语言的问题就会显现。这些问题是最基本的人性问题。人性高于一切。
作为戏剧的一种样式,肢体剧有它母体意义上的存在价值。肢体表达本身就是在试探询问语言的界限。
去年十月在乌镇戏剧节看过《孤儿》的现场演出,当时有三部国外精彩的肢体剧在演出,同样作为肢体剧的《孤儿》依旧有它独特的地方,特别是结尾处对于庄姬命运的开放处理,时隔半年多依旧可以回到当时的空间感受。演出之后和导演黄俊达聊过关于《孤儿》的创作。
《孤儿》,以及新的肢体剧作品《郑和》来到北京、天津两地演出,在北京中间剧场的排练场和他聊了新作品的创作,香港戏剧的创作状况,香港的当代变化……在最近上映的杜琪峰作品《三人行》中,黄俊达为电影设计了一幕动作戏,我们聊了这部电影,以及《树大招风》。
当天聊到最后,阿达说他正在看高行健的作品,他最喜欢《逃亡》,他也准备导演高行健的作品。问阿达为什么喜欢高行健的作品,他说:“(高行健)说的都是人性。人性最为重要。”
对于阿达和他的绿叶剧团充满期待。就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阿达和阿宛当天聊到的这本童话书)中所讲,“恰恰是实现梦想的可能性,才使生活变得有趣。”
嘉宾:黄俊达,香港戏剧导演,绿叶剧团艺术总监,戏剧作品有《我要安乐死》、《孤儿》、《郑和》、《爸爸》等。李宛虹,绿叶剧团监制。
采编:沙子龙
香港戏剧导演黄俊达
香港戏剧导演黄俊达
有时候我们的语言不太正确,身体才最诚实
搜狐文化:为什么会去改编《郑和》?
黄俊达:郑和本人是被别人强迫阉割的,而其他人想要阉割是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在宫里面生活。现在很多人其实也是“被阉割”了,为了得到一些利益,所以就把自己“阉割掉”。好多人为了一些利益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把自己的命根砍掉。我们在探索,重新让观众知道命根真的很重要,不要随便砍掉命根子,不要去追寻别人的梦,要找自己的梦。
搜狐文化:你会如何来呈现?
黄俊达:我们这个剧(《郑和》)是以郭宝昆(新加坡剧作家)的经典文本《郑和的后代》为基础。场景设定在一个办公室里面。首先它是一个故事,其实说的不仅是郑和的生活,也包括很多太监的生活。
搜狐文化:为什么会去做肢体剧?
黄俊达: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动,后来就进了舞蹈学院,然后去了法国(贾克乐寇国际戏剧学校)。在法国学习的不只是在动,还有很多语言的东西,怎么样找到一个更好的身体力量把词语连接起来。(肢体剧)其实不是不说话,重点是怎么启发身体不同的可能性,让身体越来越简单清楚,让观众有更大的空间去想象。有时候我们的语言不太正确,身体才最诚实。
搜狐文化:像《孤儿》,《郑和》除了肢体也有一些台词,有纯肢体没有台词的作品么?
黄俊达:《爸爸》就没有台词,但是里面的人物会戴面具,演出到中间,演员会把面具拿下来,然后就变成年轻时候的自己。
搜狐文化:怎么来调和台词性的语言与身体语言的关系?
黄俊达:要看主题,我先从身体方面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再找台词。像《郑和》除了肢体,也会有很多台词。我们也会用到一个物件,有时候它好像一个桌子,同时也很像一个棺材,也很像一个放太监命根的盒子,它有很多可能性。
我要安乐死:斌仔很想动,但是他不能动
搜狐文化:上次带来的是《孤儿》,这次是《郑和》,两个都是中国传统故事。会做香港本地的作品么?
黄俊达:《爸爸》就是香港的故事,我很想在舞台上呈现父亲跟儿子的关系,背景会设定在香港本地。
搜狐文化:香港近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你的创作产生影响了么?
黄俊达:会有,这些变化给了我更大的推动力,让我去思考去创作。我会去探索人性的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人是什么?人性对我来讲最重要。像《郑和》,钱(利益)还是人性更重要?为了钱可以杀你的父母吗?我很想去探讨这样的问题。这种变化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很可能是一个好的环境,如果这个世界很安静,很平常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探索的可能,我也就不会在做《孤儿》、《郑和》了。
李宛虹:比如说《我要安乐死》,展现的就是香港的状况。
搜狐文化:那个故事(《我要安乐死》)讲的是什么?
李宛虹:香港有一个人叫斌仔。03年他给特首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安乐死。
黄俊达:他在训练时候发生了意外事故造成瘫痪。他给特首写了一封信“要求安乐死”,没有得到回应,他只能瘫痪在床。他的情况让我想到,现在我们很多不同的声音,可能年轻一代对很多东西不满意,就不停地去(言语上)反抗。反抗只是其中一种方法,但是作为一个人,用什么行动去回应这个东西,不只是去反抗,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觉得比较多的人总是不停的说,但永远都不动。斌仔很想动,但是他不能动。
搜狐文化:如何来呈现斌仔的这种矛盾?
黄俊达:有一个人吊在舞台中间,很多不同形状的人,很想去帮助他。
李宛虹:但是你想想看一个病人,他瘫痪在病床上,所有人都想帮助他。
黄俊达:其实那不是帮他,可能有点在害他。斌仔在一个访问里面说,其实他很怕有人帮他,他不想有人帮他,但是他没有办法不让人帮他。他讲每一次他爸爸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非常痛苦。在我的故事里面,这些帮他的人最后把他的脑袋打开,把他脑袋里面的一些思想拿出来看。
搜狐文化:斌仔现在怎么样?
黄俊达:他最后(2012年)发烧去世了。
《我要安乐死》剧照
《我要安乐死》剧照
如果真的不能动,那会怎么样?
搜狐文化:为什么会创作这个剧?
黄俊达:2013年我刚回到香港,很多人在政府的门口,反对国民教育。我感到很惊讶,同时也感到一种很大的压力。所有人都急着去赚钱离开,对香港失去希望。我就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而不去想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如果真的不能动,那会怎么样?
搜狐文化:会有行动的盲目性与狂热性?
黄俊达:其实你可以冷静一点,有很多事情也可以做,我觉得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你自己的脑子里有很多自由。其实我们都比较没有时间让自己呼吸,就不停地去行动。
搜狐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李宛虹:我觉得是因为97回归以后那一批儿童或年轻人现在长大了,他们开始有不同的反应。对他们来说,他们以前学习的环境跟现在学习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会有很大的落差感。而对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讲就会比较适应。对他们来说,可能转变没有那么大。
搜狐文化:你会回应香港的变化么?
黄俊达:其实我的回应不是只针对香港。很多剧里面都是在讲人性的问题,人的良知问题。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看到一辆车碾过一个小女孩,很多人走过却不救她,那么这个地方就很恐怖。
搜狐文化:现实生活中会感到变化么?
李宛虹:整个社会的改变我们还挺能感受到的。
搜狐文化:比如呢?
黄俊达:一条街上本来是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店,现在变成卖金的,卖药的。
李宛虹: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去的店,我们经常会跟店的老板聊天,过去几年突然这些店都没有了,全都变成药房。我们走在路上根本不知道到底要去药房干什么。
搜狐文化:类似这种现象很常见吗?
李宛虹:很常见,我们住的地方,那个大厦楼下的商场,以前糖果只卖几块钱。现在一来找不到那种小店,二来你要买肯定要去大的连锁商店买,价钱已经变成20块,很贵。
搜狐文化:你们父母会有这种感受吗?
黄俊达:他们其实不太会理这些东西。
艺术可能是对生命的一种反抗,而不是对某一信息的反抗
搜狐文化:年轻人之中的反抗很普遍么?
李宛虹: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年轻人也说他们不看新闻报道,没有想法,无所谓的。我觉得很难说香港年轻人就是统一的一个样子,城市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人,但社会的变化是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
黄俊达:我有一个学生是北京人,他来香港上我们的工作坊,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其他学生就问,你今天晚上会去中环吗?他说我不去,没有用的。最后一天那个北京的学生哭了,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香港的街道那么干净,然后大陆好像是很发达,但是街道很不干净。他看到新闻报道,他觉得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东西,反抗得那么厉害,他就觉得很有触动。
搜狐文化:如何理解艺术的反抗?
黄俊达:我觉得(艺术)是对生命的一种反抗,而不是对某一个信息的反抗。
搜狐文化:你也做过演员,如何理解演员与角色的关系?
黄俊达:演员跟角色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能纯投入在角色之中,你必须要有演员的看法在角色里面。像彼得?柏鲁克的演员,很多都是在战火当中,有一些演员的故乡在非洲。有一次一个演员突然要走了,大家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有人入侵他的故乡,所以他一定要回家。
二十世纪重要国际剧场导演彼得。布鲁克
二十世纪重要国际剧场导演彼得。布鲁克
搜狐文化:在法国的学习给你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启发?
黄俊达:应该更加开放地真正地去探索一个题目,不是只演一个角色,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法国学习给我带来很大启发的一个点。
搜狐文化:未来会考虑做宏大的作品么?
李宛虹:我觉得不是作品的大小,作品的大小是要看这个作品需要表达什么。
黄俊达:不是因为我想做大才去想做大,而是作品本身的需要。如果有一天讲一个故事需要50人在舞台,才能让观众有一个大的震撼,我会选择用50人。
搜狐文化:你会怕重复吗?
黄俊达:不会怕重复,因为它会变成我的风格。
搜狐文化:如何来坚持这种“重复”?
黄俊达:你背后必须有一个使命感的东西在里面(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