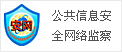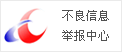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小桔灯》走笔间悉数脉脉温柔意,娓娓中仍有自持在,冰心这时候的温情是很节制的,凉得微温一盏红茶,宝色油润,香高得并不过了分,只觉得甘而顺,妥帖了五内;纵有时事影响,也全然不是大时代闷闷捂出来的不得已的老实。
配图也是文字间祥和的气质,她垂垂老去了,短发银灰色,疏疏掖在耳后,慈眉善目惯了,不做表情也意态和婉。
之后也偶然见了冰心中年和青年的相片。
中年时期的冰心,也穿得很素,模样并不摩登,整个人略瘦削了点,反而显出些幽媜色,有深闺大院里肃静的仪态,不加修饰也一身利落的清雅。
而较年轻时,冰心眉目很娟秀,端端然一张天都脸称得上清丽,神情里带一点长空淡、烟水悠悠的雅,连笑意也很工整,是有底子的大家族用清规束出来的好女儿,然而这气质太平稳了,少了点少女意态的纤纤。
冰心的女儿气,纵使家世相当,总又和林徽因的娇香淡染并不像一路,比之陆小曼的翠袖娇鬟更岔得远了,扑面只觉书卷气,然而眉眼间的从容又比早慧更深点。
早在被顾城琉璃质地烧得灼灼的诗句所惊艳,海子汗与血炼就的蛮荒情义所震撼前,记忆里最早看的便是《繁星》、《春水》,即便对于三年级的学童,这些软糯明丽的字句也是很可亲的,萋萋春生,芳草未歇,是老妪稚子都能解的悦目。
《繁星》与《春水》里的诗很透明,松散到更类似散文,轻软,澄清,檐上云结阴那样不知天地岁的明净,洗练得太口语化了,几乎带稚气,是借了几段泰戈尔的风骨的。
泰戈尔的诗则是哲理化后的天真,读来确实满纸一派天然,这天然是玉骨本天然,不是借人力,更是花气天然百和芬,是久经了冬的历练才有的春,风光霁月是怜惜着养出来的。
也是长者浮游天地一概收入了囊中的智慧,用诗情提炼后去芜存真的那点真。
这真里自然有最初的心动,也有乍然的欢喜, 欢是浅淡的清欢,有鸟去岂为听 的禅意,这遗憾与怅惘,多的也单只是风来不可托的无可奈何,痛也痛了,但不深,沉成鹅卵石,日积月累给磨柔和了棱角,氤氲了日光水韵后触手也玉脂温,这石头心到底也是硬的,想来是润着湿意的一点迟钝的痛楚。
冰心的诗,是孩童极温吞的一颗心,是新生那种孜孜的欢悦,对一切好奇,望见所有都觉可人可爱,纯粹得甚至称不上是善,因为连恶都尚未见识过的,唯有耿耿。
之后却也见了冰心的一首宝塔诗,笔触很轻快,写她那清华教授夫君吴文藻: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这段宝塔诗写得很俏皮,挑选的一截截也是生活闲趣,倒有些垆边女儿不解愁的娇憨,因为文人气,倒可爱甚于茜袖女儿簪野花那种明丽带野性的娇痴了。
冰心文人气重,万卷堆床书才练就的字有千钧,逢到了燕石变做至珍,和其夫吴文藻先生做了一世一双人。束发便考入清华,未及而立,早捧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而归。胸蟠翰林才调,一奠是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基。
学者识真,吴文藻先生到底难逃书生习气,生活中颇有些梁武憨痴达摩呆,因而夫妻间调笑事不少。
冰心于《只求凡人的幸福》里淡淡一笔,依旧是平和的态度,语意温馨地写了宝塔诗的由来。
“马”和“羽毛纱”源自抗战前,一日这对如胶投漆的夫妻一道归宁北京城,冰心爱子心切,便支使吴文藻上街给孩子买些 “萨其玛”解馋,幼子尚用语牙牙,不会说萨其玛,只说“马”。因此吴文藻行至铺子里,也只会说买“马”,唬得铺员成了丈二和尚。冰心纯孝,欲为购置其父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为拜谒岳父大人,吴文藻先生奉夫人冰心之命吴文藻入了“稻香村”点心店和“东升祥”布店,这书生吴文藻到了店铺,开口便要“马”其“羽毛纱”。店长听闻只觉莫名,所幸吴文藻先生声名播得尚远,店长也识得,便致电了冰心,才弄清这场乌龙之原委。 而“东升祥”的店员一句“您要买一丈多的羽毛纱做什么”的纳罕也惹得冰心和其父都捧腹,冰心评说“他真是个傻姑爷!” 其父只笑说 “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又一次,冰心拿了一束丁香花,其夫不认识,只问此为何花。冰心有心一耍女儿态,便诓他是“香丁花”,吴文藻深以为然,故此一直唤丁香花为“香丁花”,改不了口。
时值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一双夫妇也赴约拜访冰心及吴文藻,于其云南呈贡家里一度周末,冰心玩心起而即兴赋宝塔诗如前,梅校长耳闻此诗此事也不仅抚掌而笑,于公与私,都替这清华大学出身又返巢任教的同僚出一出头,便依样续了两句:
只怪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能配交际花
书呆子怎能配交际花
梅贻琦冠号“寡言君子”,又绝不止步于谦谦,常年所奉“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能卸了“慢、稳、刚”的戒备,横生了妙趣,舌绽莲花地一次反唇讥,必也是深知冰心雅量,未有他疑。便和冰心作诗调笑吴文藻一般,是故作顽劣态的稍越轨,微愠都是佯装,来掩一掩会心一笑。
之后偶然翻到冰心一则小短篇,陶奇的暑假日记。边读边忍俊。
陶奇,谐音淘气,是文人惯会的一点文字游戏,很寻常,稀奇的是,冰心拟男童稚语,惟妙惟肖,仿得很逼真,浑然初解语的活泼。
絮絮的言语平铺直叙,用词亦很单薄,然而不过分,笔力犹在,照旧是一字千钧的准,然而半点略成人化的遣词也无。
童话与寓言的确美,好比安徒生或者奥斯卡怀尔德。
夜莺彻夜啼唱,用心头最温存的热血,一换冬季最初也是最后一朵猩红玫瑰,这丰腴的甜香比闲愁还无计奈,任东风千丝万缕也吹不解;麻苎衣衫的仙度瑞拉,娟娟楚腰,被挥水晶魔杖的神仙教母呢喃几句咒语,妆不入时世,掩映霓裳,襟袖皆仙姿。
酒美春浓花世界,当然美煞人,连颜色都是一截一截从虹彩上取下来的,明丽得过了分,兼又带点湿漉漉的甜香,袭人,即便熏得人醉了,也是一晌睡痕留醉袖的酣梦,是成人气质很浓重的。
这样的暗涌太荡气回肠了,即便把所有跌宕压缩得玲珑了,玲珑成幼童睡前含的那颗蜜枣,也是几蒸几晒经了市面,再甜些也是千帆过尽有余味,太味厚了些,各种滋味孩童也品不全。
这些更像是大人说给孩童的故事,总被隔膜了一屏风的声色,孩童雾里看花地贪觑几眼,心性好比玩万花筒,是对另一个斑斓新世界的渴念,然而终究是水中花镜里月,看得再熟听得再顺耳,到底也摸不到抓不实。
然而冰心的全然孩童气的暑假日记是就近可得的,如案头书,窗前柳那样自然,可了意,更贴着心的。
行文里的悠远更像水,东风吹水琉璃软那样的新鲜澄净,不为读来增几成韵律,就添几多累赘,她把成人化的思维和声口剔得很干净, 几乎像初生,但诗意仍旧初荷出水那样清嫩地来了。
童心本身就是一阙诗,美过少年游。
顾城也做到的,写的诗朗朗如日月,因为底是最纯粹的白,什么都还未沾染,再淡薄些,都衬得秾丽了,何况顾城下笔断无节制,是铁了心洋洋洒洒,拼尽最明艳的色调,浓涂重抹,这样活泼泼的五色相叠里,几乎有盲人下了毒的艳绝,教人看得人心软。
解了他一心一意的偏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唯要做一个叛逆的顽童。不肯长大一分一毫。
而冰心所偶然一露的纯真则相反,是因为她太懂得了,成熟得有慈悲气,她是真能出世也能入世,更通达了。
大概正因为如此,冰心做宝塔诗能和平辈文人得趣唱酬,也能体贴了孩童世事不谙的未雕琢,这实是颇难得的。都言观书妄,冰心却不,她的入世缘有才情作底,更有仁厚生成的谦逊,冰生玉水云如絮,冰心就有这样的净如练。
不然也不会于《只拣儿童多处行》中这般写,“我想起两句诗, ‘儿童不解春何在,只拣游人多处行’,反过来也可以说,‘游人不解春何在,只拣儿童多处行’。”。
这便也是她能依依耐了性子,潺潺写《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这类儿童文学的初衷吧。
冰心自有的大气,并不被她蓄意体贴了稚子的儿童文学给冲淡了,调子是温存的,然而文理仍极理性且清洁,是见过大阵仗又看淡了的,有这底气撑住了人,才明白冰心这谦和的温婉意。
到底是上可继前圣,下可慰赤心的。
作者:钱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