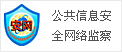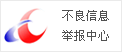2015年10月29日,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古坡乡魏家坪村,41岁的魏祥祥正在接父亲的电话,由于至今还孑然一身,好多活儿父母都安排他去做。魏祥祥家里7个兄弟,他排行第七,哥哥们都结婚了,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了,魏祥祥单身至今。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
2015年10月29日,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古坡乡魏家坪村,41岁的魏祥祥正在接父亲的电话,由于至今还孑然一身,好多活儿父母都安排他去做。魏祥祥家里7个兄弟,他排行第七,哥哥们都结婚了,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了,魏祥祥单身至今。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编者按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 一,这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会多出生20多个男孩。如今,那些在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年代诞生的孩子正在陆续进入婚龄。
20多年来,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有的这些因素交织影响着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作为一个曾高度城乡二元化的国 家,其“婚姻挤压”更多地挤向了边远、贫困地区,数千万“剩男”的婚恋难题正引发更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发展,事关权益,在迈向全面小康的攻坚战 中,不应被忽视。
2015年,中国青年报派出多路记者分赴豫、冀、湘、鄂、皖、甘、桂等省区贫困农村,并会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 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专家,历时半年,对中国农村剩男问题进行了全景调查,现推出全媒体深度报道,预警社会,并以期引起更多关注和扶助。
腊月细碎的雪花化在了年味逐渐升腾的豫东韩朱岗村,邓孟兴家里格外热闹,大多是头发花白的父母领着腼腆的后生,话题只有一个:“他叔,俺儿子年纪不小了,你留意给寻个媳妇吧。”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10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绍对象的活儿没法干。
可老邓10多年来当媒人的名声还在,家里有男孩的还是会趁着年轻人打工回来过春节的机会,在腊月和正月里频繁出入老邓家,拜托他帮着解决终身大事。
“还有6个小妮儿。”老邓对村里谁家有适婚的女孩了如指掌,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姑娘,很难看得上村里那40多个未婚男青年,“还有条件更好的小伙儿从外村找来呢”。
2010年之前,老邓一年还能撮合成十几对,但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曾经密密麻麻记录着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儿的信息在不断增加,女孩儿的信息越来越少。
老邓总结说,估摸着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远远多过女孩。其实,老邓朴素的认知早已经是人口学家研究的重点。
过去的10多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断对人口普查信息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对全国28个省(区、市)300多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整体失衡。
近一二十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厘清了一个事实: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路走高,并持续高位徘徊。最高峰的时候,出生性别比高于120,远超107的正常值,一度成为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李树茁等人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逐渐显现。”李树茁的判断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 压”,“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 多。”李树茁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被迫失婚”的大龄剩男密集出现
相亲成为春节主旋律的远不止河南的韩朱岗村。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夫妇提起3个儿子的婚事也是长吁短叹。
王飞龙自己有3兄弟,这3兄弟又分别有3个儿子,9个男孩都到了适婚年龄。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近四五年来春节前后的主题就一个,拜托能找到的一切社会关系,安排一场又一场的相亲。
每年还不到腊月,王家的几个妯娌就开始四处奔走,张罗相亲的事,但能安排相亲的女孩实在太少,大多数时候,男孩们只能在网吧里无聊地度过。尽管各种网络社交工具也曾让一些农村男青年有机会在虚拟的环境中实践爱情兵法,但毕竟那大多是镜花水月。
9个男孩的相亲波折几乎让这个家族每年春节都被愁云笼罩,大一点的那几个孩子已经奔着30岁去了,按农村的习俗,过了30岁还没娶上媳妇,打光棍几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媒婆生意难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龄剩男密集出现,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近年来在国内多个村庄做田野调查,他观察到,一些农村的光棍率之前较为平稳,但从8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上升,“这个现象非常显著”。
他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计算出,一些村里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个简单的估算,全国农村在峰值期大约有2000万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将有近30个剩男。
李树茁团队对300多个行政村的实地调查显示,每村平均大龄未婚男性达9.03人。其中,近80%的大龄未婚男性身体健康,没有残疾,“他们的失婚不是身体原因造成,属于被迫失婚”。
每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都会要求研究人员写篇回乡记。在这些乡村笔记中,几乎所有学者都把经济拮据列为农村剩男失婚的最根本成因。博士生刘锐曾讲述过一个辛酸的过年故事。
2014年春节,刘锐的同乡、37岁的邓长清没有回家过年。邓的母亲曾生过几场大病,家里没能积攒下多少积蓄,因此小邓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 希望趁年轻挣点娶媳妇的钱。然而由于学历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几年下来,仍然没能脱贫。父母也曾找人介绍,但媒人看到小邓的家境,都摇头不愿接单。
不知不觉人到30,小邓逐渐感受到单身的压力。最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单身,年终回家不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邻居也会指指点点,父母每谈及此事就 长叹。有一年,全家吃完团年饭,母亲借着酒兴提及此事,说着说着竟落下泪来。小邓对家里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给家里打电话,决定不回来了。他 说,现在找到一位带着两个小孩、即将离异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后人少时带着媳妇回家。放下电话,母亲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愁云笼罩了整个新年。
“现代婚姻鼓励个人能力,但个人能力由家庭文化决定,当经济上既处弱势,家庭教育又不足时,光棍就会被惯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刘锐写道,“回到村里,长辈说得最多的话是,农村人要面对现实。”
争夺新娘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王飞龙自己就是24岁结的婚。“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倡导晚婚的标语,乡上也得等你到24岁才给办证。可没想到,如今儿子这个年纪谈婚事就已经晚了。”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回,王飞龙的父亲那一辈也是在十八九岁就得娶妻生子,那时候早婚是为了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间的晚婚光荣之后,到了王飞龙儿子这一辈,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挟着回到早婚的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该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来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过春节时,魏程琳意外地发现,18岁的堂弟阿坤已经订完婚,阿坤的父亲海叔正在实施下个计划,给16岁的小儿子张罗相亲。
海叔掰着指头给魏程琳比画,现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处于相亲阶段的男孩子有10个,女孩却只有4个,你不抢,别人就下手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都22岁了,还没找着对象,家里人为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绍说,在他的家乡,春节前后,青年们陆续回村,许多人在这一个月内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见面、定亲和认亲、结婚全部走完。“办完没有证的婚礼,就各自外出打工,谈不上了解,年轻人是完成个任务,老人则是卸下副重担”。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在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来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
由于女性资源稀缺,争夺新娘的范围被扩大。“现在农村离婚妇女也很抢手。过去农村离婚女性大多被嫌弃,但现在也成了被争夺的对象。”
律师姬如松老家也在豫东农村,他告诉记者,村里去年离婚了12对,女的很快全都被抢走又结婚了,男方则只有3个再婚,其余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12个人里有个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师的说法得到了媒人邓孟兴的证实。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妇女都很枪手,“带着拖油瓶也没关系,因为彩礼要得少,越是离婚的,找过来说媒的越多。”老邓说:“我们这儿,离过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给媒人的礼钱都要多些。”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的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姬如松告诉记者:“身体残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门槛,只要是女的,怎么样的都能给说到婆家。”
在豫东一个村庄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一户人家就因为无力给二儿子支付昂贵的彩礼,只得给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里人怕她跑丢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关在屋里,吃饭时,再把她放出来。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几乎不与她一起生活。但对其父母而言,儿子成家结婚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有老婆总比打光棍好吧”,年迈的父亲苦笑着对记者说。
一个笑两个哭
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3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这样的解释让王飞龙哭笑不得。他年轻时候找媒婆介绍对象时,如果说谁家兄弟多,那绝对是加分项。
那时候,如果没分家,男孩多,壮劳力多,挣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实。即便结婚分家了,那谁家的兄弟多,能帮衬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话语权。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场上要减分。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说,同村20岁的阿亮就更惨了,他家里4个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没有媒人愿意上门。他奶奶说,人家女方家庭一听是兄弟4个,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魏程琳感概说,也就这十来年功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媒人邓孟兴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 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 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 “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 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强大。在豫东的孟庄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传宗接代,惟此为大呀!”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 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
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饥不守道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邓孟兴说,春节前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门口能同时停着四五辆车,车里满满地坐着四五位后生,都排着队,等着和女孩见面。
姑娘每天的时段已经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来,就坐在家里等着不同的媒婆按着时间段带着他们手里的男孩上门来。遇到姑娘觉得条件不错、顺眼的男孩,她会多聊几句,留个QQ号,加个微信。看不上的,冷场几分钟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离开。
邓孟兴说,往往是他领着的这几个男孩还没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催促,该人家的时间了。
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男孩并不新鲜。邓孟兴印象中,有一个女孩一个春节就见了100多个男孩。
“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总算百里挑一定下一个。可没想到,不多久,两人就吹了。来年的春节,大家听说这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这一回,又见了90多人。”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生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每人收费5000元。”
在皖南一个村庄,记者听说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贫穷,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眼看按常规结婚无望,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以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 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历代的村规民约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 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 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宣金学、向楠参与了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责任编辑:徐童 SN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