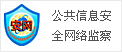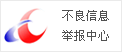最近颇为不顺利,整天烟不离手。
老婆关心,说记得你以前挺喜欢踢球的,要不你去玩玩,权当散心。我摸了摸肚腩,说你看我这肚子都怀孕6个月了,怎么踢?
老婆说现在不是什么什么杯嘛,你看看球赛吧。我吐了一个烟圈说算了,没精神熬夜,再说家里宽带太慢,那4K电视完全就一摆设。
隔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家里面多了一个4K机顶盒——原来这几天联通在小区做活动,她去办了个宽带,弄了个4K机顶盒。她得意地说:这次能高清了吧,我们一起看,我也想看看中国队的表现!
我哭笑不得,只能说好,有中国队比赛的时候我叫你。
6月12号凌晨,威尔士打斯洛伐克,当看见拉姆塞的时候,我恍惚了,我知道他曾经断过腿。
我的左脚踝开始隐隐作疼。

八岁那年,我们小镇有了第一个足球。
于是记忆里有无数个球后黄昏:斜着杀出的光线温柔地把这个小镇熏黄,特别是把小学那面红色的砖墙抹上了如同燃烧的颜色,显得特别不真实。
几年之后,我在那面砖墙上看见了罗纳尔多的海报,我问同行的小伙伴:他是谁?
小伙伴面对夕阳背对我,用一种末日高手的口气说:罗纳尔多是外星人,也是一个英雄。
那个时候的我年幼无知,对英雄还带有幼稚而天真的崇拜。我对自己说,好,那我也要做一个英雄,像罗纳尔多那样,跑在所有人的前面。小伙伴摸了摸自己的光头,咧嘴一笑,说明显是他像罗纳尔多一些。
后来,每次踢球我都要跑在最前面,我用英雄的梦想鼓励自己,和我一起奔跑的还有那个小光头,本来他叫邓永生,但他坚持所有人都要叫他邓尔多。
就这样,周雨凇和邓永生,一起求学很多地方,也一起闯荡过很多球场。然而,球王只有一个,巴西的9号也只有一个。上大学之后,因为我们都坚持要穿巴西9号,最终只能分别加入球队,各自为战。
2007年的某天,西南大学,黄色的巴西对阵绿色的巴西。在一次中圈反抢的时候,一个身影的从我身后飞铲,在我倒下的瞬间,我听见了我左脚踝的骨头裂开的声音,我也同时看清楚了那个人——邓永生。
那年我大三。
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而直到半年之后,我才再一次碰足球。邓永生无数次小心翼翼地把足球传到我左侧,但我永远都是别扭地用右脚去接球,后来,我对他说:我可能,也没那么喜欢足球。
邓永生抱着足球,沉默不语。
我拍了拍他肩膀,转身离开了球场。
从那以后,我和邓永生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原因无他,是因为我去球场的时间越来越少,终于从某天开始,尽管我们还在同一个城市,我却再也没见过邓永生,我也再也没有踏上过球场。
电视屏幕里,拉姆塞跌跌撞撞地突破,混了一个助攻。我心里憋得慌,跑去阳台抽烟,不远处,零零碎碎有点灯火,邓永生是不是也在看球?
我狠狠抽了一口,用力把烟屁股忍了很远,摸出电话,找到那个熟悉的名字,打了过去。
我说:“兄弟,你还看球吗?”
他说:“看啊,现在就在看。”
我说:“要不到我明天到我家来看吧,我刚弄了一个4K机顶盒,连腿毛都看得清楚。”
“好。”他顿了顿说:“明天我们有场球,你要不要来,我们还差一个前场队员。”
我叹了口气。
电话那头死一般沉默。
.......
“当然要来!但我要9号!我要9号!再说一次,我要9号!”
“你他妈要10件9号球衣都行!只要你来”
“但是我很久没踢了,停球估计都要停三米远,就像一条狗啊。我怕坑了你。”
“有我邓尔多在,什么时候怕过?”
时间低眉,我好像又看见了那个小光头,站在红色的砖墙前面,告诉我他要做一个英雄。
(责任编辑: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