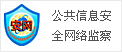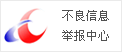这千年万年沉寂的阳光,给这天海闷得太久,活泼得类似过分热情的乡下人,没有遮拦。
一行人伛偻着背,并列沉默地走,沙石很平稳地发出咯吱声,很像远古的农民,是一次现代向野蛮的开荒。
渐渐行到了山脚,一节节的楼梯长得吓人,又太陡了些,倒竖着的节肢动物,不用张牙舞爪也够叫人冷气倒抽一口。
随行的小孩倒是异常兴奋,噼噼啪啪一路小跑。
西方人特有的洋娃娃形态小人儿,稀松的绒绒金发,奶浆白的皮肤,整个是嫩藕节拼成的加拿大小挪吒。
人小,更显得楼梯长,天阶样走也走不完,而且配的还不是月色凉如水,是日光汹汹,虎视眈眈对着人。
然而他小马驹似的,噌噌噌冲在前面,横穿沙漠也用不完的那股喜孜孜的生命力。
好容易走完了木制的阶梯,便来到一个极简陋的小凉棚,草木味被蒸腾着,虚虚掩掩会袭人。
虽然连松棚黯黯都算不上,不够断云障日,然而凉意微微已经够可贵。
而况还有半角天海公路可欣赏。

少了雾,山再连绵也不大鬼影憧憧,只仿佛晒多了太阳,汗津津俏皮相。
看着不大像阴雨淫淫的温哥华,仿佛是某个不知名热带城镇的一截剪影。
太暖烘烘,太好脾气了,没有给风云雨雪浸润过似的爽朗。
车子轰轰地来了,很有点类似过山车,但是更短,斩头去尾过的,也有点像孩童版小火车,因为线条完全圆嘟嘟,看着不严肃。

看着非常年轻。
他正了正头顶的安全帽,让我们也选。
鸡子儿白柠檬黄的安全帽堆作两箱,把自己缩小再缩小,好装作最巨型的比巴卜糖果,假装在货箱里等着被领走。

那位浅玻璃色眼珠的小男孩用一种慎重极了的表情,挑挑拣拣出一顶湛蓝的安全帽,好跟他的衣服配。
安全帽都有些脏了,泞着些些泥渍,倒也不觉得污秽,因这是大自然的污迹,和人为的总两样点。
戴着白色的安全帽,最厚最沉实的鸡蛋壳半蒙着头,结实得几乎能听见思想的回音。

给麾下鼓舞士气似的,他鼓圆了眼睛和腮帮子,极富兴味地问谁之前来过。
太平易的问题,被他迪斯尼员工那种敬业好客的派头撑一撑,也有趣起来。
那位小可人儿的爸爸高而瘦,筋肉练得很结实,举猫咪似的把他举高了,和讲解员说,当我和他这样大的时候,我同爸爸妈妈来的。
现在我们陪他来了。她妻子的声音愉快得要滴了蜜,当然她整个人也是野蜂蜜罐里泡大的,浑身是麋鹿一样的结实,整个人深金棕,浅色的睫毛长得像太阳绒绒的金线。
怀里母兽样的反背着一个更小的婴孩。

白生生的小男孩虽然也像个小玩意儿似的被逗弄着,但他是更大型的娃娃,会咯吱咯吱笑,作为对他父母及讲解员对话的呼应。

她摸着自己鸭蛋黄的安全头盔,并不去答讲解员的问题。
或许她觉得自己成熟胜过小男孩与解说员,已经能用热情以外的态度回应这个世界了,并不用如此喜形于色。
她站得这样镇定,连解说员夸张形容车的鸣笛声堪比巨人雷震的吼声,也没有动一动眉毛,只是歪着头平稳地听,小猪眼里有审视的光。
青少年的生活,即使仅仅是静止地站立不做动作,也仍旧飞速又蓬勃地生长着,比春草更悄然也更迅疾。

硫磺,铁锈以及翻涌的泥土味被矿洞里风卷过来,总觉得是什么奇遇的开端,连气味都刺激又新奇。
位置很小,一道蜜奶黄的小窄条,是童话里小座椅的款式,椅背倒不矮,直愣愣托着人,但也只能容下两位成人。
踏板很坚实,灰闷闷的泥锈痕里,雨后微型新蘑菇样一顶一顶最小的小圆帽,每一枚都是一个按钮,按全了才能通向地底奇幻世界。
也没有设什么安全护栏,大概车的年代实在久了,用了又用老成了古董,反倒成了景观的一部分。

鸣笛不特别长,然而为了矿道是桶形,又并不短,回音四面八方涌过来,几乎有嗡嗡感。
是千万只地底隐形的蜂蝶,久不见人,把人都做了花,亲昵昵扑过来采。

石壁作暗赭色,汨汨渗着水,被莹莹的灯火色矿灯照着,明暗深浅都是天然,根本就是一副巨型五代山水画。
虽然褪点色,也写意太过了。

大片湿莹莹的凹凸浓淡赭色块里,这一点点神秘的兰翠,有小心翼翼的漂亮,被鱼鳞状铁死亡一扭一扭格着,更类似美人鱼最纤巧的尾巴微光里微微一漾。
是暗海里阴沉沉的好看,然而不安定,仿佛有危险性。
深深的山腹里埋了极小的海,是山神凄凄一滴泪吞进了肚里,和胸中的块垒落在一处,都消不去。
讲解员忽然变了声音,用一种近乎戏剧化的悄声,说要关灯了。

讲解员的安全帽和游客两样点,多了一盏极小的灯,加上光晕也不比鸭蛋大,悠悠地暗淡着,是被碾过的短蜡烛将熄。
他又胖大,所以更像安康。
不过他的身子倒很有一种和外形不大匹配的轻巧,很灵活就闪到了一壁矿墙下,拧开了一只煤气灯,照出了大开的保险柜。
保险柜四方形,郁郁嵌在石壁重,也不小,足够放下几本大英词典。

讲解员圆而短的粉扑子脸,被黄得泛赭红的灯光熏着,并不现全貌,配着他笑呵呵的高嗓子,很有残酷童话,黑暗迪斯尼之感。
他也很知道,甚至享受这短短刹那的恐怖。
你们谁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放在铜像里的。他的短脸孔被光影托起来,忽然类似起远古被下了魔咒的浮凸面具,对着虚空振振有词,很有股杳杳度微茫的望孤帆神气。

解说员特意端着灯,焰焰的光像滴了涩雨,暗如灯花,他凑近了“爆炸性杂志高危”的字样,高声地读。
是炸药啊。小男孩短促地惊呼,大概是听出了小男孩声音里的害怕,他立时开了灯。
矿壁上平平放了深朱的木箱,在矿洞里浸久水气,拨灯书尽那种黯淡的红笺色,好像泪痕丝丝还未干。
淋漓的大白字,被一格一格的条栏截着,不大工整,虽然是平平写的,却总仿佛有点浮凸着。

听了有点恻然,即使我也只能想象。
黑黢黢的地底世界里,黑暗俨俨地包过来,无休无止的阿刻戎河裹住了人,举着蜡烛的矿工能见者的光亮总是和爆裂声相伴。
每一声都像盘古开天辟地。
然而他们也不是巨人,对深而巨大的矿洞而言,他们是人形的炸药筒,错落着挤在满溢了硫磺气味的长坑中,飞速地消耗生命力。

被讲解员握在手里,像是他双目炯炯捧着一头刚出土的巨型瘦蜜蜂,榨尽脂膏后肚子瘪瘪的,针头还是一样,自有股煞气。
讲解员言之凿凿这些十九世纪的老物件,直到现在仍能用,一个机器负责横向钻孔,另一个则负责纵向钻孔。
这些钢铁蜜蜂,极扎实地咬入矿层,汨汨地吸着金属与矿石,震天响地吮走山神的血脉。

为了黑暗,短短的时间被拉得更长,声音大到实体化,是人为的雷霆,长着有啮齿动物的牙,错错落落刺咬着人。
即便停止了,太阳穴也一阵一阵尖锐的跳痛。
声音非常大吧?讲解员摘了厚耳罩,大概也未从余音里恢复过来,说话声音特别响,像是远古的人住在不同的山头,得提了气呐喊,声音才够滚滚传到另一边。
他接着说,之前很多开矿工人都是极年轻的男孩,不到二十岁,便已经耳聋了。
众人听了脸上都有点不忍。
那位胖墩墩的青春期女孩,别过了头,摸着她细亚麻的马尾,没有说话,两颗实心玻璃灰眼珠有余烬的颜色。同情心的颜色。
凿下的矿石是累累的小碎块,需要运送,两个矿工每天得用工车云十五吨这样的石。

它是古董,也是长老,年高德勋,也还能用一用,能干得动。
大家都没说话了。
快出矿洞时候,见着远处茫茫白圈像是日出,光亮渐渐盛了,雪月交光的炯炯。
日头底下的风也一样可亲,软熔熔地吹来很远,闻得出金黄色太阳的干燥,愈闻愈是草木气方苏,更有人间样。
出了山洞,清风暖日醍醐一样灌结实了人,像是忽然开了窍,耳聪目明,只想纵酒山南千日醉,看花剑外十年狂。
然而能醉酒总需酿酒人辛勤,种花、铸剑都要费尽人间东风、万斤铁,都不易。
淘金有千淘万漉的艰苦,开矿也一样有吹尽狂沙的艰辛,能成事都个人有个人的辛酸,而我也已工作了月余了。
欢迎您下次再来,或者带着您的孩子来。解说员还是一脸迪斯尼招牌式的笑脸,小眼睛眯缝着,好像是愉快,又好像是怕太阳太大。
我看着他慢慢地山路上走,那种软和的弹跳性仿佛不见了,大概是他的胖裤腿和沉靴子太笨重了,于平地上走总不大相宜。
很奇怪,这一路我只看着他的短圆脸蛋矮身子,脸颊鼓鼓,健康又快乐得可以做谷物早餐代言人,却没发现他的背影是这样疲倦,连他的圆滚滚也近乎河豚生气了的一种自卫,不大具有什么实质性,像是虚张声势。
我忍不住看了他很久,他很像一匹不快乐的熊。
作者:钱雪